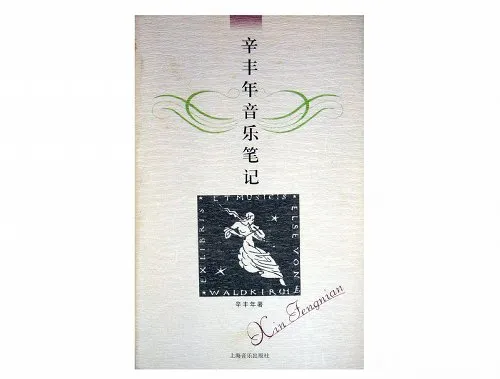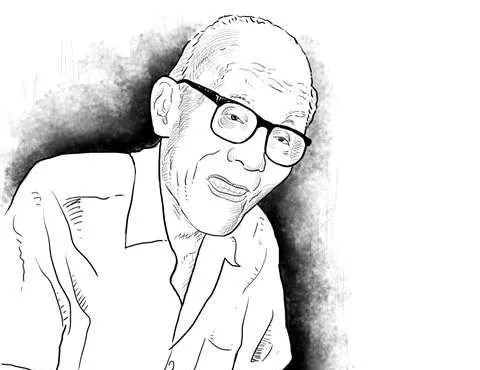找到与辛丰年相关的文章资料27份

如果不是倾听西方音乐,接触了不同风格的异域音调,可能自己也就不会对音乐的中国味发生兴趣,从此有意识地“寻味”。听了古琴曲,见到赵元任的《新诗歌集》,才懂得还有“中国味”这个题目。《新诗歌集》真是可怀念的一本书!

对比国内和国外的音乐会现场,有一个有趣的现象:西方古典音乐会的观众席,远望都是一片银发,而中国来听古典音乐会的人,却都还是黑发满头的年轻人。这也是国外古典音乐人士非常羡慕中国市场的一个理由——中国古典音乐的市场才刚刚兴起,至少还要蓬勃发展50年。但也正因此,国内古典音乐的爱好者,非常渴求音乐欣赏普及的知识……

在辛丰年的葬礼上,播放的是老先生钟爱的德沃夏克《新大陆交响曲》的第二乐章。严锋在悼词中说:“父亲一生忠厚老实,善良正直,在艰难卓绝中把我和弟弟带大。他参加革命不是出于投机,而是想奉献社会,他在任何时候都从未停止对真理的追求,从未失去对世界的信念。父亲毕生都在追求大爱大美……”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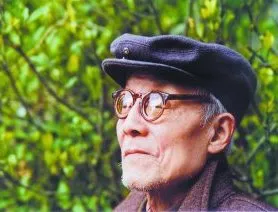
辛丰年先生走了。 有人将此视为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《读书》杂志为代表的优美文风的一个告别式。我则并不那么悲观。我以为,一种优美文风,正如潮之起落,月之圆缺,不可能总是圆满,却也不容易真的消逝。到一定时候,它又会重现光华。中外历史上,有“古文运动”,有“文艺复兴”,这都是借过去时代之文、之艺……

开门时,83岁的辛丰年一身干净的灰蓝色毛装扣到领口,可能经过有西洋趣味的裁缝的改编吧,袖口果如大儿子严锋在那篇序言里描述的:“常有油迹,做家务弄的”,头戴渔翁一般的风衣帽子,像旅行时的老作家。但屋里并没有风,下午中的下午,既听不见音乐,也不见那些浓缩的薄片紧密地陈放着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