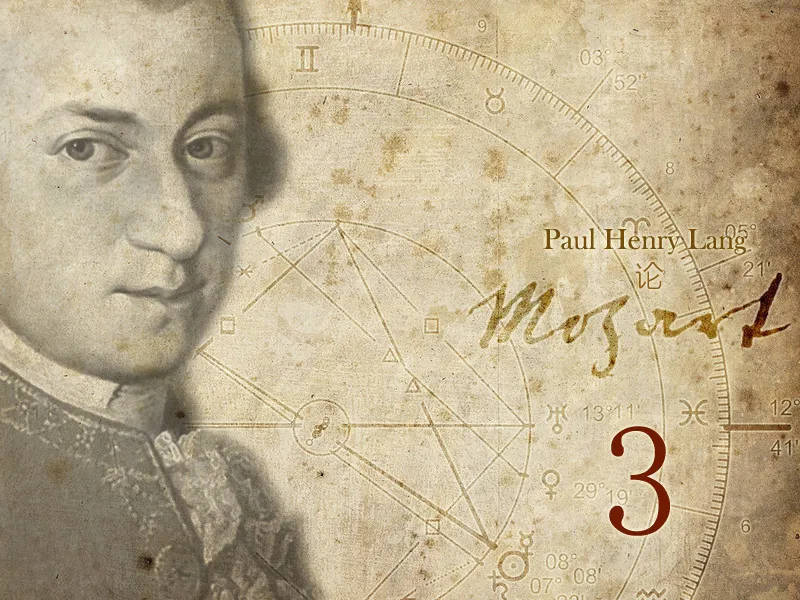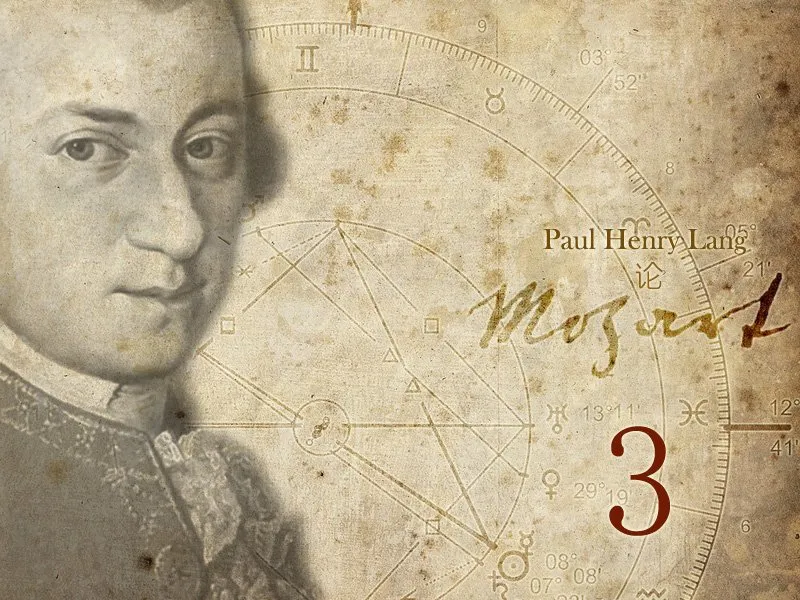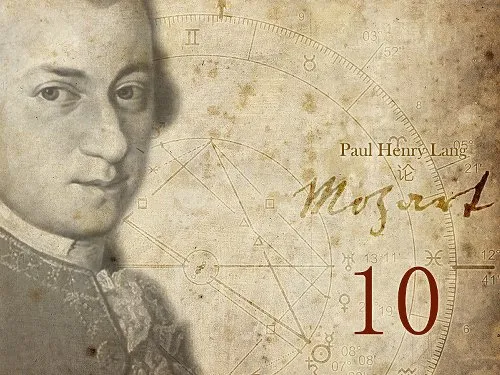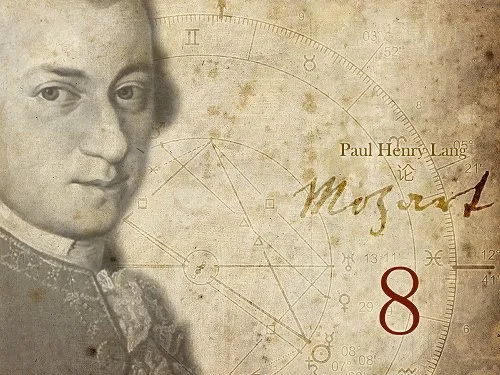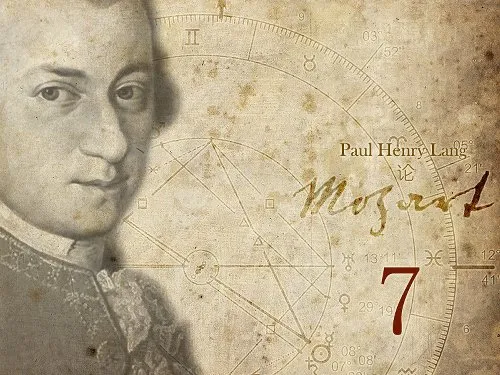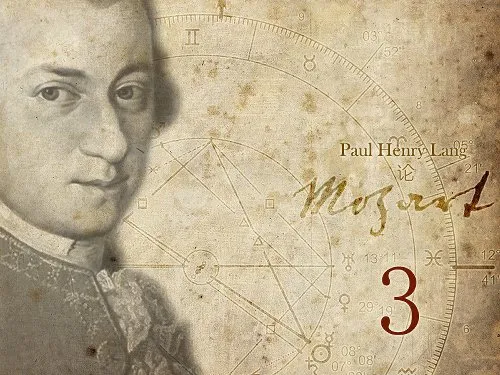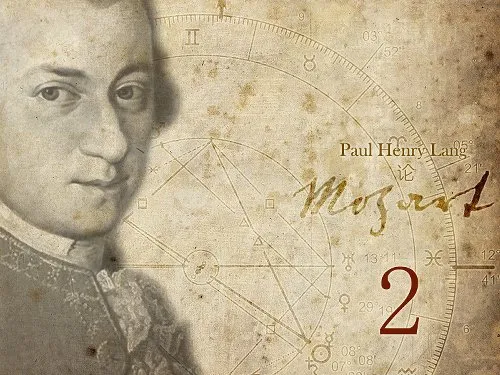无论意大利的印象多么深刻,莫扎特并未忘怀自己的奥地利故乡。他有几位同胞好友,他们的音乐令他赞叹。有一位名叫万霍尔,具有“大胆、狂野的作曲家”的美名;另有一位加斯曼,从业于闻名遐尔的波洛格内斯神父,其歌剧第一次显示出奥地利和意大利的迷人融合——而这将变成莫扎特的第二天性;还有最重要的,性情柔和的迈克尔·海顿。随后,新的启示降临:约瑟夫·海顿。在他身上,莫扎特突然发现了音乐中的天才。以前,他通过克里斯蒂安·巴赫无可挑剔的形式美和旋律美,悟得异质的元素可以被融为一体;现在,他明白这还不够,为了企及艺术作品的完整性,艺术家必须殚思极虑。他的交响曲篇幅加大,逻辑增强。现在他确信自己能够成功解决所遇到的艺术问题,因而他允许主观情感具有更为宽广的驰骋天地。
在G小调交响曲(K. 183)中,伟大的莫扎特已经站在我们面前。这部交响曲浑然一体,概念及其实现都无懈可击,其中不可思议地混合着感官性的旋律美与恶魔般的激情,显现出莫扎特悲剧性的一面。景仰莫扎特的人,发现莫扎特这般年少已品尝人间悲哀,不免唏嘘感慨。从海顿那里,莫扎特发现乐器也有灵魂。因而大量的器乐作品蜂拥而至:协奏曲、交响曲、四重奏、为新式的槌击钢琴所作的奏鸣曲、以及数量最多的嬉游曲和小夜曲,变化之丰富无以言表。这都是专为特定的合奏而写的“应景之作”,但恰恰是这种“应景”的性质,莫扎特音乐的理想主义精髓才易被人感知和触摸。因为,虽然现实得到公正评价,但现实又被包裹在理想世界的庄重、幽默和反讽里。这种应景音乐给他提供了机会,让他撩起幕帘,查看一眼生活的某个旮旯角落。
由于莫扎特在萨尔茨堡的处境得不到改善,他辞去主教给他的差事,再次上路,不过由母亲陪同。在几处稍事停留,他们到曼海姆呆了相当长一段时间,那里有很多老朋友在等着他们。滞留曼海姆,莫扎特又遇到一批富于刺激的音乐家:霍尔茨鲍尔、神父福格勒和斯特克尔,还有卡纳比希,更别提难以置信的曼海姆乐队的吸引力。1778年3月,莫扎特又到了巴黎,但是这时四处查看巴黎和它的音乐的莫扎特,已经不是那个对一切都感到新鲜好奇的孩童了。无疑,法国喜歌剧、格鲁克与皮钦尼的作品依然赢得他的尊敬,但总的来说,他并不掩饰自己看不起法国的音乐生活。
法国的音乐总罩着一层文学的光环,格鲁克派和皮钦尼派在理论和美学上纷争四起,莫扎特的纯音乐想象对这些都嗤之以鼻。他的歌剧计划告吹,但访问巴黎却产生了不同寻常的器乐作品。虽然法国音乐的理性主义倾向远非他所好,但法国人冷峻的美学清醒态度却再一次提醒他,一种同质的风格在艺术上极具优越性。法国喜歌剧生动、质朴的音乐和出色的宣叙调朗诵法也让他心动。他风格上的集中,异质因素的融合,在正歌剧《克里特王伊多梅纽斯》(1781)中特别明显。这部作品似乎已位于他成熟风格的入口。尽管莫扎特的正歌剧概念尚不清晰,但其中法国因素和意大利传统相互调和的方式已经宣告,最伟大的音乐戏剧天才正在到来。
莫扎特移居维也纳。约瑟夫二世计划建造一座国家歌唱剧剧院,现在大功告成。莫扎特接受委约,创作一部德语舞台剧,选用一部原先曾由安德烈谱过曲《后宫诱逃》作台本。莫扎特建议对这个本子进行重大修改,以便可包容较大篇幅的歌剧因素。1782年6月,紧跟《后宫诱逃》成功首演之后,莫扎特与他自己的康斯坦茨结婚(《后宫诱逃》中的女主角恰巧也叫康斯坦茨——译注)。在正是从这一年开始,莫扎特开始了与海顿之间亲密无间和相互促进的友谊。
这部歌唱剧演出之后的四年,是成年人的岁月,其间这位自由的艺术家将天职化作每日的劳作,将艺术的实际操作与理想境界统一起来。一方面,他从生活的材料中有条不紊地建造自己的艺术;另一方面,他用他的艺术组织自己的生活。现实中要面对许多问题:婚姻、养家、在社会中寻找位置。家庭生活的插曲,与朋友和同行的社交,促使他写下大量应景歌曲、卡农、三重唱、以及其他小品杰作,其精美典雅只有歌德的《交游之歌》(Gesellige Lideder)可望其项背。他忙于生计,钢琴学生、公开音乐会、所谓的“学社”活动,监管自己作品的出版,以及其他的聚会和活动都占用他的时间,而每项“应景活动”都会带来一批作品的诞生。
具有贵族背景的维也纳音乐生活极其发达,为室内乐提供了适宜的温床。在海顿所谓的俄罗斯四重奏影响下,莫扎特创作了六首四重奏(K. 387、421、428、458、464、465),以深挚之情将这些作品题献给他的良师益友。莫扎特强调说,正是从海顿那里他才学会“应该怎样写作四重奏”;但是,在聆听这些新作品后,诚恳而宽厚的四重奏大师却对利奥波德·莫扎特说,“我以自己的荣誉担保向您发誓,我认为您的儿子是我所听过的最伟大的作曲家。”在早年的室内乐中,莫扎特将十八世纪的社交音乐带至变化多端、五彩纷呈的境地。D小调钢琴协奏曲、G小调钢琴四重奏、C小调钢琴协奏曲、C小调钢琴奏鸣曲和幻想曲,在这些作品中,一种全新的、异常阴暗的基调占据上风。新方向的天空上,有一片阴影,那是约翰·塞巴斯蒂安·巴赫的天才。但是不必刻意去寻找细节上的引录或回忆,因为巴赫的天才影响莫扎特并不在于具体的例子。
早期从业于神父马蒂尼的对位课程已强烈地触动过他,他已经很快就相当熟练地掌握了复调作曲法。在范·斯威腾男爵——此人是一位有名的乐迷,曾为海顿翻译《创世纪》的英语歌词——的府第中,莫扎特在巴罗克最后一位大师的作品中懂得了如何理解复调。范·斯威腾是一位巴赫和亨德尔的热切崇拜者,他在音乐会之前的聚会中(帝国首都里最好的音乐家往往都来出席)组织演出两位大师的作品。莫扎特一定领悟到这种音乐是德奥音乐精神的化身,他的下意识想象中回响着这种精神,有时在他的教堂音乐中具体的表现出来。
现在,德奥音乐的复调文化以其全部的伟大风貌展现在他眼前。他对这种新发现的强烈兴趣体现在一些作品中,开始是将巴赫的几个赋格改编为弦乐四重奏(K. 405),随后是像C小调双钢琴赋格(K. 426)这样的巍峨大作,再后是最末一部C小调弥撒,很可惜没有完成。这首弥撒紧接《后宫诱逃》而作。这一巧合意味深长——作曲家通过德语歌唱剧进入创作的新阶段,其后紧跟的是一部圣乐,前一部作品对生活的回响消解在德奥复调的精神之中。然而,以这种风格写作的作品大多没有完成,说明莫扎特对维也纳和意大利的效忠仍更强烈,对德奥的遗产更多是渴望,而不是继承使用。直到生命的晚期,莫扎特才成功地调和这两种截然相反的风格体系,才真正将德奥传统化为自身。